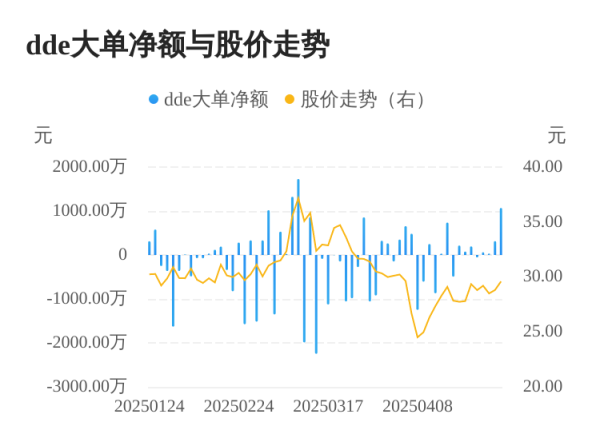内容介绍
1992年,我就开始注释《论语》,至今三十几年了。2004年以后,我的主要精力更是用在研究和注解《论语》《孟子》的疑难字词句上。这里只讲《论语》。2016、2018年,出版了《论语新注新译》繁体本、简体本,到今天总共印刷了14次,马上又要重印了。这书的特点和精华,都体现在其中的考证上。研究的时间,“十年磨一剑”还不止;而且运用了两条腿走路的方法,就是训诂和语法相结合。我的导师郭锡良先生说它是“殚精竭虑”之作,“在杨伯峻《论语译注》的基础上,无疑又跨进了一大步”。北师大孟琢教授说该书“代表了自语法以通训诂的最高成就,让经典文本语境的考察具备了严密可信的语言规则”。
在上大有关领导和上大出版社领导的关怀下,经过责任编辑不厌其烦的努力,这部《杨氏新译注论语》出版了。该书在《论语新注新译》基础上又有所改进,具体有以下几点:
1.进一步去粗取精,还有首次面世的《考证》(十几项)。《论语新注新译》,不论繁体本、简体本,考证部分,都较为精炼。平均每项《考证》,繁体本不到2000字,简体本1000字出头。这次出版的《新译注》,每则《考证》平均只有七八百字。这是因为,《论语新注新译》的读者是研究者和准研究者,需要较多的例句来支撑;本书是研究的入门版,艰深的例句要尽可能地少。
展开剩余95%《论语新注新译》繁体本、简体本的《考证》分别为160多项、190多项,最近刚刚交稿的第二版《论语新注新译》的《考证》多达220项,同样为了照顾初学者,本书从这220项中精选了136项。也就是说,有若干《考证》是首次面世的。
2.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适合初学者。本书不但和《论语新注新译》一样在《导言》中介绍了方法,还在一些关键的《考证》末尾画龙点睛地总结了本考证所运用的方法、手段。这同样较为适合初学者。
3.《论语新注新译》有两句话:“阳春白雪的内容,下里巴人的形式。”本书更加贯彻了通俗化特点。具体就是《导言》更加通俗易懂,引人入胜;《考证》末尾画龙点睛的点评也较为口语化,生动活泼。
此外,《论语》二十篇,每篇末尾,还请专门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杨柳岸老师撰写了导读,这样有利于学习者了解该篇的思想主旨。
举两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
1.小不忍则乱大谋
一般都把这句的“忍”解释为“忍耐”。据全面统计,当时“不忍”不带宾语时,都是“不忍心”的意思。意思是小小的仁慈,足以败坏大事情。汉代人也确实是这样理解的。在书中我们举了汉代大臣袁盎用这句话劝太后,他说,溺爱儿子最终会害了他。很幸运,太后接受了意见。
2.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现在一般的解释是,人要是没有恒心,当个跳大神的都不够格。本书经过全面考察,当时的“恒”,应该解释为“操守”;“巫医”也不光是跳大神的,而是并列结构,分别指“巫师”和“医生”。另外,对“人而无恒”的解释,本书也是首次发表的。
导言
读懂进而注释古书,语言的历史性、社会性、系统性原则很重要;与此相关的,还有“分布”和“审句例”等概念。
本《导言》前三分之二篇幅是《杨氏新译注论语》《杨氏新译注孟子》共同的,所以例证也主要采自《论》《孟》两书。
先说语言的历史性。语言是缓慢而持续地变化的,无论其中的词汇、语音还是语法,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举个例子来说,《庄子·秋水》“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的“望洋”,一本很著名的《庄子》注本是这样注的:“‘望洋’一词有多种解释,旧注作‘仰视貌’……然‘望洋’作常义解即可。‘洋’即海洋,上文云‘北海’可证。”
可是,“洋”之有“海洋”的意义,是迟至北宋才见诸载籍的;它出现在汉语里可能比北宋早,但不可能早到《庄子·秋水》成文的时候。古汉语字典记载得清清楚楚:“洋,大海(晚起义)。”孙德宣先生有《释“望洋”》论证这一点。
要尽量避免望文生义,其中一个法门就是要注意语言的历史性。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某学者对古书中某个字的解释不满意,说,我觉得应该解释为什么什么。但他未必想过,该字的该意义那个时代是否已经产生。
不但词的意义古今有别,语音、语法也一样。读者诸君能够建立“语言是逐渐变化的”这一概念,思过半矣。
* * * * *
语言是用来交际的,说的话就要让别人听懂。以《诗经·邶风·击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为例,它最初是用来表达战友情的;假设今天99%的人理解它是用来表达爱情的,1%的人理解它是用来表达战友情的,当然要以那99%的人的理解为准了——对它的理解在历史的长河中产生了变化。变化了的语言是没法人为地纠正的,这叫做“语言符号的强制性”。语言要以说这种语言的人通常的理解为准,否则就听不懂,没法实现交际的功能,这就是语言的社会性。如果说指鹿为马,或者指米奇为唐纳德,都是行不通的话,蛹化为蝶,水冻成冰以后,还要叫它们为蛹、为水,也都是行不通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有人主张古书中字的意义要以《说文解字》为准,但你能肯定古书中某字的意义就没有在《说文》所记载的基础上产生变化吗?既然以《说文》为准也不见得正确,那该如何是好?一句话,释读古书要依据语言的社会性原则。
* * * * *
语言的社会性这一原则,怎么运用于释读古书中古今见仁见智的疑难词句呢?语言的社会性制约了说汉语的人只能把雪的颜色叫作“白”,把煤球的颜色叫作“黑”,而不能颠倒过来;到百度上搜一搜“白”和“黑”,会出现数以万计的“雪白的婚纱”“漆黑的夜”之类的对“白”和“黑”的描述。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一个常用词,它的某个意义,总会在同时代典籍中留下痕迹,所谓“雪泥鸿爪”是也;它的变化轨迹,也会在不同时代的典籍中草蛇灰线伏延千里。
就拿王力先生所举的一个例子来说好了。他指出,《曹刿论战》中“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的“间”,有的书解释为“补充或纠正”,但《左传》中“间”出现81次,另外80处都不当“补充、纠正”讲,其他先秦两汉古书中“间”也从不当“补充、纠正”讲,“左丘明在这里不可能为‘间’字创造一个新义,因为这样的‘创造’谁也不会看得懂。作为一个原则,注释家不会反对语言的社会性,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注释家却往往忽略了这个重要的原则。”(同上)
这一“间”当然是参与、厕身其间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掺和”,这样的例子在同时代典籍可是一抓一大把的,这就是“留下痕迹”。
* * * * *
上面,我们谈的是语言的历史性、社会性问题,至少不比历史性、社会性次要甚至更为重要的语言的系统性问题,我们会在后头说到。
说到这里,要谈谈“分布”了,否则好些问题讲不清楚。分布,一是指句法成分在句中所占据的句法位置,如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等等;二是指句法成分的结合能力,即该成分修饰什么成分,该成分被什么成分修饰,等等。通俗地说,就是词语在特定句子中的上下文条件。比如考察《卫灵公》“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不是考察“忍”而是考察“不忍”,就是因为“忍”和“不”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后者会“限定”前者以什么意义出现。我们并没有否定“忍”的“忍耐”义,只是想考察“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句中“忍”的意义。既然该句中“不忍”是一体的,考察时就要把这一“条件”考虑进去。
一个词,它的多义,是呈现在字典词典里的;在特定的上下文中,它必定是单义的。也即,上下文锁定了该词,让它只能呈现一个意义。换言之,分布限定了词义,分布就是特定词义的标志牌。也即,若要求得在某一上下文中的某词到底是呈现其甲乙丙丁几个意义中的哪一个,只要弄清楚甲乙丙丁四种意义各自的分布特征(也即上下文特征),然后按图索骥,看所考察的词句的上下文和甲乙丙丁四种上下文中的哪一个相吻合就行了。杨树达先生把它叫作“审句例”。我曾发表过一篇《以考察分布为主轴的训诂》,文中说:“该词的某一类分布特征和某一意义是一对一的,就像身份证号码对应每个人。这就等于说,以考察分布为主轴的训诂,能使得这一研究具备可重复性、可验证性——几位学者分开来研究同一疑难词语,将得到大致相同的结论。”
这就是所谓“经典阐释的确定性”和“分布分析可以使意义形式化”(分别见孟琢《论中国训诂学与经典阐释的确定性》,载《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7期;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3页)。
* * * * *
古代训诂大师虽然没有分布的概念,但他们的经典范例,无一不与分布理论相吻合。例如高邮王氏父子对《诗经·邶风·终风》“终风且暴”的考证:
家大人曰,《终风篇》:“终风且暴。”《毛诗》曰:“终日风为终风。”《韩诗》曰:“终风,西风也。”此皆缘词生训,非经文本义。“终”犹“既”也,言既风且暴也……《燕燕》曰:“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北门》曰:“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小雅·伐木》曰:“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商颂·那》曰:“既和且平”)《甫田》曰:“禾易长亩,终善且有。”《正月》曰:“终其永怀,又窘阴雨。”“终”字皆当训为“既”。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五,又见《经传释词》
上文证明了,在“终~且~”这一上下文条件下,“终”呈现类似“既”的意义。这很好地说明了“分布”是如何锁定意义的。由于“终温且惠”“终窭且贫”“终和且平”“终善且有”等句中的“终”都呈现类似“既”的意义,同一格式(即同样的上下文条件)的“终风且暴”的“终”没有理由不是这一意义。这就符合语言的社会性原则。
利用分布锁定意义的原理,利用语言的社会性原则,就能够在特定条件下,由此及彼,由一般推知个别,综合归纳分析古书中疑难词句的意义。
这一例也符合语言的历史性原则。因为语言是变化的,所以由一般推知个别时,要用同时代的书证。该例用来证明“终风且暴”意义的“终温且惠”“终窭且贫”“终和且平”“终善且有”等书证,都与前者是同一时代的。
* * * * *
下面这例大家应该不陌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译注》译为:
如果人们所喜欢的没有超过生命的,那么,一切可以求得生存的方法,哪有不使用的呢?如果人们所厌恶的没有超过死亡的,那么,一切可以避免祸害的事情,哪有不干的呢?〔然而,有些人〕由此而行,便可以得到生存,却不去做;由此而行,便可以避免祸害,却不去干。
本书关键的不同在“何不用也”“何不为也”两句。包括《孟子译注》在内的其他注本理解为“什么不使用呢”“什么不干呢”,我们理解为“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不做呢”,意义正好相反。
其理由,一是,先秦典籍中的“何不V”,都是“为什么不V”,未见可理解为“什么不V”的。也即,“何”用于任指表周遍义(类似“他啥都好”“什么都新鲜”中的“啥”“什么”),当时语言中未见,是晚起的语言现象。到了汉代,“何”可以表周遍义了,汉末的赵岐也就用后起的语言现象来解释“何不用也”“何不为也”了。
二是,“由是”意为“因此”,它是顺承上文的。如果译为“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不做呢”,下文“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正好顺承上文;而译为“什么不使用呢”“什么不干呢”,“由是”却是逆承了,这与它的一贯用法不符。我们的译文是:
假如人们想要的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一切可以求得生存的手段,为什么会有人却不去用它呢?假如人们所厌恶的没有比死亡更不堪忍受的,一切可以免除祸患的事情,为什么也会有人却不去做它呢?由此可知,〔有时候分明〕可以活下去,也是会放弃的;由此可知,〔有时候分明〕可以避免祸患金河配资,也仍会坚守的。
这是典型的运用语言的历史性原则进行疑难词句考释的例子,也就是杨伯峻先生所谓“从汉语史的角度”来考证疑难词句。《孟子·梁惠王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的考证也是如此。
* * * * *
下面这例用以说明语言的社会性原则。
《孟子·滕文公下》“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6.10-1)两句中的“李”,杨伯峻先生说:“井上之‘李’,为李树,还是李实,很难肯定。《文选·张景阳杂诗》注引《孟子章句》作‘井上有李实’,姑从之。”我们认为,这一“李”指李树。
一是,先秦典籍中出现的“桃”“李”“梅”“苌楚”等植物,当下文出现“实”(果实)时,都是指桃树、李树、梅树、羊桃树等,如《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有蕡其实。”(程俊英《诗经译注》:“茂盛桃树嫩枝枒,桃子结得肥又大。”)
二是,先秦典籍中“有李”“有桃”“有梅”等“有+植物名”格式中的“植物名”,都指该植物本身,而非指其果实。如《秦风·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程译:“终南山上有什么来?又有山楸又有梅。”)
三是,若此“李”指李实,则此句当为“井上有李,螬食之过半矣”;也即“有”的宾语,在下句再度出现时,一般要以代词“之”指代。例如《孟子·告子上》:“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
以上三点,都是基于语言的社会性原则,基于“分布”的原理,从当时语言中抽绎归纳出规律,再以之解决具体词语问题的。
由一般推知个别的做法,体现的就是语言的社会性原则。
* * * * *
再用两个例子来说说“分布”。
《论语·述而》:“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子罕》:“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这两处“何有于我哉”历来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解释,一是“对于我有什么困难呢”,这是自信之辞;一是“〔以上优良品质〕我又具备了哪一点呢”,这是自谦之辞。在《论语新注新译》里,我们论证其意义为:“〔如果具备了以上优良品质,〕我又算个什么呢”“〔如果具备了以上优良品质,〕我又算得了什么呢”。
以下各例可以证明:“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沈玉成《左传译文》译“何有于二毛”为“管什么头发花白不花白”,也即“头发花白算什么呢”)
“吉若获戾,子将行之,何有于诸游?”(《昭公元年》,沈译“何有于诸游”为“何必把游氏诸人放在心上”,也即“游氏诸人算什么呢”)
“将夺其国,何有于妻,唯秦所命从也。”(《国语·晋语四》,邬国义、胡果文《国语译注》译“何有于妻”为“娶他的妻子又有什么呢”,也即“娶妻又算什么呢”)
“君若不鉴而长之,君实有国而不爱,臣何有于死,死在司败矣!惟君图之!”(《楚语下》,邬、胡译“何有于死”为“我又何惜一死”,也即“死又算什么呢”)
以上几例都大致与《论语》时代相同,这就符合语言的历史性原则。由一般推知个别,符合语言的社会性原则。最为关键的是,不管是一般还是个别,都是放在“何有于……”的格式中来加以考察的,这就是“考察分布”。
* * * * *
下面这个例子更能说明考察分布的妙处。
《孟子·离娄下》:“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后三句《孟子译注》译为:“只要能推求其所以然,以后一千年的冬至,都可以坐着推算出来。”这是以“缘故”义释“故”。朱熹《四书集注》:“求其已然之迹,则其运有常;虽千岁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这是以“故事、成例”义释“故”。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左传·庄公十年》)“故因其惧也,而改其过;因其忧也,而辨其故。”(《荀子·臣道》)“其吏请卜其故。”(《吕氏春秋·季夏纪》)“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季秋纪》)以上各例“其故”前的动词如“问”“辨”“卜”“知”都是感知动词,“故”都是“缘故”义。
“若治其故,则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左传·成公十一年》,沈玉成《左传译文》:“如果要追查过去的情况,那么它是周天子属官的封邑,您怎么能得到它?”)“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庄子·外篇·知北游》)“欲治其法而难变其故者,民乱不可几而治也。”(《韩非子·心度》)“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商君书·更法》)以上各例“其故”前的动词如“治”“求”“变”“法”都是都是行为动词或状态动词,即非感知动词,“故”都是“故事、成例”义。
“苟求其故”的“求”与《知北游》“无求其故”的“求”一样,都是非感知动词,所以“故”为成例义。
因此,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天极高,星辰极远,如果能弄清楚它们恒常的轨迹,以后一千年的冬至,都可以坐着推算出来。”
我们对《论语·为政》“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考证与此相仿。“攻”在先秦汉语中,有“攻击”“进攻”义和“从事某事,进行某项工作”的意义。两者在分布上的区别是,前者的宾语是人和地,后者的宾语是人和地之外的事物。“异端”属于后者。
* * * * *
我在《论语新注新译》(简体版)的《前言》中写下了一些话,觉得照录就可以:
著者的具体做法,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1.书证归纳格式,格式凸显意义。2.一个剥离,一根主轴。3.两个突出。
上引王氏父子之释“终风且暴”,是对“书证归纳格式,格式凸显意义”的最好说明。
一个剥离,一根主轴,是对为何要采用以上方法的解释与说明。剥离,指将语言外部证据如情理、义理、历史事实等等从主要证据位置上剥离开来。这牵涉到语言是一个系统的原理,这里不拟展开。我们只要知道,词的意义,与情理、义理、历史事实等并无直接关系;也即,情理、义理、历史事实等并不能限定词义。因而,仅仅依据这些来判定词义进而判定句义,是不可靠的。
主轴,指以考察分布为主轴,其他如形训、声训、义训以及二重证据法等等方法、手段都围绕着考察分布这一主轴来进行。
两个突出(双突出),一指在语言系统外部证据和语言系统内部证据中突出后者,一指在语言系统内部证据中,突出通过考察分布,即审句例所得的证据。不难看出,两个突出,不过是对著者上述做法的较为精炼的概括罢了。
还有一句话,是借用电影名,叫“一个都不能少”。也即,几乎所有的训诂方法和手段,著者都“不抛弃,不放弃”,只是通过双突出,确定了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顺序而已。这样,当不同证据发生矛盾产生龃龉时,就知道坚持什么,放弃什么。
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看若干训诂教科书,以上方法手段往往是平列的,都被强调的。当好几位学者分开来研究同一疑难词语时,甲主要采用这方法,乙主要采用那方法,丙又主要采用另一方法,自然,结论也就各自不同了。这在以前,是允许的,都“可备一说”,都“新义迭出”,都算好成果。
如前所述,上下文(分布)将“锁定”某词的某意义,要了解特定上下文中某词到底是什么意义,可以通过考察该词不同意义的分布特征来做到。也就是说,该词的某一类分布特征和某一意义是一对一的,就像身份证号码对应每个人。这就等于说,以考察分布为主轴的训诂,能使得这一研究具备可重复性、可验证性——几位学者分开来研究同一疑难词语,将得到大致相同的结论。
* * * * *
上面这一段,信息量有点多,读者可姑且放在一边。下面来谈谈语言的系统性问题。语言是一个系统,这是语言学的入门级问题。在语言是系统这一问题里,又有一个入门级问题,它显得那样微不足道,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它不值得专门一谈,附带提提就行。王力先生在《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说:
假定这种研究方法不改变,我们试把十位学者隔离起来,分头研究同一篇比较难懂的古典文章,可能得到十种不同的结果。可能这十种意见都是新颖可喜的,但是不可能全是正确的。其中可能有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因为它是从语言出发去研究的。
为什么从语言出发去研究,结论就是“正确的”?因为语言是一个系统。
一般的语言学概论教科书,当然也谈语言是系统,一般讲的都是语言是符号系统、语言是分层级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等等。
系统学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都曾是一门显学。它有一个基本原理: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联系是较为直接的,频繁的,紧密的,而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稀少的,疏松的。也即,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强,系统内部与系统外部之间的关联性弱。根据关联性越强,越有可证性的原理,求证系统内部的问题应当主要依赖该系统内部的证据。所以,“从语言出发去研究”,就能求得正确结论,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语言的各子系统内部,就是语言系统内部;这是语言系统的边界。
* * * * *
因为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不大提它;因为不大提它,所以常常忽视。
因此,需要重申,在语言系统外部证据和语言系统内部证据中,要以内部证据为主。语言系统外部的证据不能作为主要证据,更不能作为唯一证据。
因此,语言系统内部证据是自足的,是不可替代的;语言系统外部证据是非自足的,不是非有不可的。
在语言系统内部证据中,因为分布特征能够锁定词的意义,所以在考证疑难词句时,又要以“审句例”即考察分布为主。这就是所谓“双突出”。
语言系统外部证据,虽然在主要证据位置上被“剥离”了,但它还可以作为次要证据。
分清了主次,遇到矛盾产生龃龉时,就能很好地处理了。比如主要证据支持一个结论,次要证据支持另一个结论,就采纳主要证据支持的结论。
例如“小不忍则乱大谋”,有的证据支持忍耐说,但那多是语言系统之外的证据,遇到语言系统之内的证据支持忍心说,次要证据就要让路。这还是因为分布能限定词义,语言外部因素不能限定词义。
这样一来金河配资,“经典阐释的确定性”就有了保障,也就落实了“分布分析使意义形式化”。
* * * * *
还有个问题需要说说。
如前所述,1.句法成分(例如词)在句中所占据的句法位置,也即它所充任的句法成分,如主语、述语、宾语等;2.修饰关系(或“结合能力”):该成分可修饰什么成分,可被什么成分所修饰。以上两点的总和,就是该成分的“分布”;这个,也叫作“分布总和”或“分布特征集合”。
陈保亚说:“每个词都有自己独特的分布特征集合……每个词都有它自己特定的分布总和……没有任何两个词的分布是绝对相同的,每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分布,形成分布个性。”(《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研究》,第33-44页)也即,每个词都有一群区别性分布特征,把该词和其他所有的词区分开来。我们将这个称为“大范围区分”。“大范围区分”既不具备可行性——见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古代汉语是无法呈现当时语言中每个词的每一分布特征的,因为某一时代的文献不可能囊括当时的整个该语言;也不具备可操作性,因为这样做十分繁琐,事倍功半;而且没有必要,在进行词语考证时,没有必要将该词与其他成千上万的词区分开来,仅仅需要与其他一两个词,或该词其他义位区分开来。
某词的某一区别特征,或它的两三个区别特征,足以将该词与其他一两个词,或该词的其他义位区分开来。我们将之称为“小范围区分”。
* * * * *
例如,《左传·庄公八年》“袒而视之背”,阮元《校勘记》认为当读作“袒而示之背”。有些学者赞同阮校,有些认为应如字读。著者的学生李瑞在《左传》和同时代语料中找到“示”“视”各几十例,“示”能带双宾语,且近宾语为“之”的有十馀例,远宾语是人体某部位的有五六例;而除此之外的“视”只能带单宾语。由此可知阮校可从。这里仅考察了关键的分布特征,便得出了可信的结论。
上文所举诸例,也可说明这一点。
小范围区分,具有可操作性。
一般规律,一个词与其他一两个词区分,或与该词其他义位区分,其间意义差别越大,越容易区分。以人打比方,一男一女,容易区分;两男一老一少,也容易区分;两男年龄相仿,一高一矮,也容易区分;年龄身高相仿,一胖一瘦,依然容易区分。但有些双胞胎小孩,穿一样的衣服,就不容易区分了,需要在细节上仔细辨认。
“视”和“示”,在分布上是容易区分的。而“故”的“缘故”意义和“故事、成例”意义,以及“攻”的“攻击、进攻”意义和“从事某事、进行某项工作”意义,就不大好区分了。对于后者,尤其需要仔细地考察分布上的细微末节。
* * * * *
总结一下。
语言的历史性:语言是逐渐变化的。在释读古书疑难词句时,要以变化的观点看问题。
语言的社会性:语言要以说这种语言的人通常的理解为准。在释读古书疑难词句时,要用同时代文献中的书证来予以证明。强调“同时代”,是兼顾语言的历史性。
语言的系统性:严格区分语言系统内、外证据,以语言系统内部证据为主要证据。
因为分布可以锁定词的某一意义,用来证明的同时代书证必须与被证格式相同。例如搜罗“终~且~”的句子来证明“终风且暴”的意义进而证明句中“终”的意义。
具体做法可归纳为:1.书证归纳格式,格式凸显意义。2.一个剥离,一根主轴。3.两个突出。
这样,当语言内外证据或语言内部不同证据发生矛盾产生龃龉时,就知道主要采纳哪些证据。
“大范围区分”和“小范围区分”的划分,使分布理论运用于古书疑难词句释读具有可操作性。
* * * * *
再简要介绍一下有关《论语》的知识。必须说明,下文多采自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可知:“论语”的“论”是“论纂”(有顺序地编排)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若干学生言语行事的一部书。“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的。
《论语》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连。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的作者有孔子的学生。有些篇章,还出自孔子的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其中不少是曾参学生的记载。这样,《论语》的著作年代便有先有后了。这点,在词义的运用上也有所反映。譬如“夫子”一词,早先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指称对话者,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相当于“他老人家”,只是在《阳货》中有两处例外。由此可见《论语》的成书,是跨越了至少好几十年的。
《论语》一书的最后编定者,应是曾参的学生。因为,1.《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较孔子其他弟子为多。2.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参最年轻,而且有一章记载着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8.4)。孟敬子是仲孙捷的谥号,则这一段记载之为曾子弟子在孟敬子死后所记,应无可怀疑。因此,《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
* * * * *
《论语》传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的本子:(1)《鲁论语》20篇;(2)《齐论语》22篇,其中20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3)《古文论语》21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400多字。《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为根据,号为《张侯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今天,我们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就是《张侯论》。后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侯论》。《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馀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直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
《论语》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它。汉朝人所注释的《论语》,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127—200,《后汉书》有传)注为较多,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残卷,也就十存四五;其他各家,在何晏(190—249)《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现在《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注疏》就是用何晏《集解》和宋人邢昺(932—1010,《宋史》有传)的《疏》。
除敦煌及日本唐写本残卷外,1971年,定州汉墓《论语》出土;2015年,南昌海昏侯墓《论语》出土。这些都是研究《论语》不可或缺的。
* * * * *
关于“论语”的读音,《经典释文》卷三:“论语,上如字,又音‘伦’。”上,指“论语”二字的“论”。如字,就是通常的读音lùn。也就是说,论语,读作lùnyǔ,也可以读为lúnyǔ。“论语”现在的读音,根据语言的社会性原则,通常读作lúnyǔ。但“论”通常读lùn,读作lùnyǔ,又有《经典释文》可资依据,应该也不算错。我的导师郭锡良先生,就读作lùnyǔ。
有关《论语》的书,可谓汗牛充栋。读者如果认为看了本书之后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几种书:
(1)《论语注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经注疏》中。
(2)《论语集注》——宋代朱熹(1130—1200)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合《论语》《孟子》为《四书》,自己用很大功力作《集注》。朱熹对于《论语》,不但讲“义理”,也注意训诂,故这书无妨参看。
(3)《论语正义》——刘宝楠(1791—1855)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作《论语正义》。后因病而停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1821—1880)继续写定。所以这书实为刘宝楠父子共著。广征博引,加以己意。该书是清代学者注《论语》最有成就的著作。只因学问日益进展,昔日的好书,今天便可以指出不少缺点,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小。
(4)程树德(1877—1944)《论语集释》,征引书籍达680种,虽仍有疏略可商之处,因其广征博引,故可参考。
(5)杨树达(1885—1956)《论语疏证》。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时出己意,加案语,值得参考。
(6)杨伯峻(1909—1992)《论语译注》。张政烺先生说:“在今注中确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的,可以达到雅俗共赏的境地。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论语》《孟子》成书较早,杨注虽对于典章制度的注释小有不足,但其解决难点,疏通文意,都有独到之处。”
(7)蒋绍愚(1940—)《论语研读》。用语言学知识解读《论语》疑难字词句,结论大多正确。
* * * * *
本书是《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繁体本、2018年简体本)的精简本。必须一说的是,继《孟子新注新译》第二版完成出版以后,《论语新注新译》第二版也已完成,正在润色过程中。该书增加了若干新的考证,其中一些为本书所采纳,如1.13“言可复也”、5.13“夫子之文章”、5.21“其愚不可及”、5.26“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6.3“今也则亡”、6.5“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8.7“士不可以不弘毅”、9.27“子路终身诵之”、11.26“浴乎沂”、17.7“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18.6“而谁以易之”、20.1“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新注新译》第二版中,有的考证做了重要的补充,也为本书所采纳,如2.6“父母唯其疾之忧”。
本书是给学中文学和学对外汉语教学的本科生、研究生量身打造的,因此,《论语新注新译》中比较繁琐的考证没有选入,只是在注释中稍微涉及。入选的考证,也删去了许多例句,只留下了为了说理而必须保留的。
同时,为了教学,加了些画龙点睛之语,对考证所涉及的知识稍微作了讲解。
每篇之后,还由专治中国哲学史的杨柳岸博士撰写了导读,俾读者能大致掌握该篇的要旨。
这样一来,本书对于所有读者来说,就更具有普适性了。
发布于:黑龙江省易速宝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